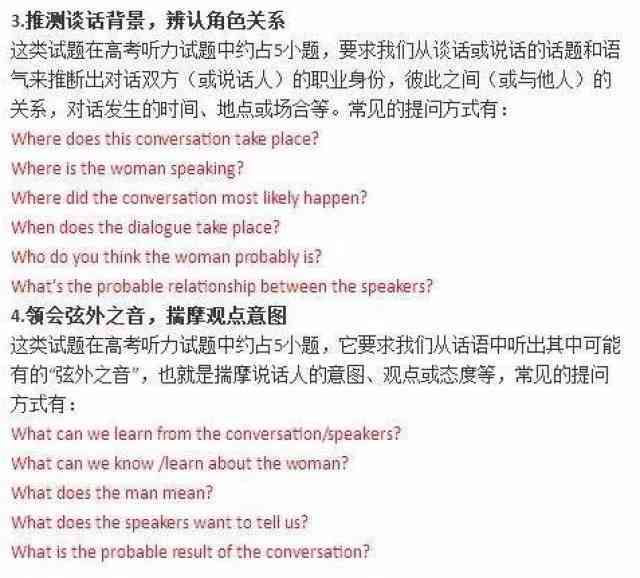一九二三年春夜,大提琴家比阿特丽斯•哈里森在自家花园里练琴时,不知哪里突然冒出一只鸟,啁啁啾啾,似在跟她斗曲。比阿特丽斯很好奇,以琴声回应,几个回合后,鸟声适应了琴声,争斗变成合奏。她往上,鸟声跟着拔尖,她向下,鸟也随之噏半嘴,始终保持着和谐的三度音程。这体验前所未有,比阿特丽斯在日记中形容,“鸟声像一股炽热电流穿透全身,直至头发和指甲”。这只鸟对音乐的准确性、灵活度以及跟她配合的默契,竟可媲美她在皇家爱乐乐团的同行。第二天她去找园丁,也是她的邻居,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羊毛灯笼裤都穿反了,听到这消息,狂喜大叫,差点摔倒在地砖上。他说,那只鸟是夜莺,俄耳甫斯之子,天生的歌者。他小时候就见过这只夜莺,他父亲唱圣歌时,夜莺就会在窗前踯躅,以鸣声应和,久而久之,成了旧识;他还捕过蝗虫、飞蛾和椿象来喂它。后来他父亲过世,鸟就飞走了,他再也没见过,直至比阿特丽斯的琴声引它归来。
他说,这茫茫几十年间,也不知夜莺去了哪里。想必它去了火山极地,越过海心,去无穷远,哪里都去过了。夜莺不单声喉了得,它更有天下无双的耳朵,隔着万里也能听见,因此两个月前比阿特丽斯在这里练琴,拉的第一声琴响,就已经惊动了它。它飞那么远回来,就为了应和比阿特丽斯那时候的琴声。它对好音乐真是痴迷啊,拜托拜托,别再让它离开了。
两个月前,练的是哪首曲子,比阿特丽斯已经不记得。爱德华•埃尔加的《在南方》?戴留斯为她新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声音一经产生,就变为幽灵。消失是声音的宿命。比阿特丽斯对园丁的说法也很怀疑。鸟的寿命有那么长吗?更有可能的是,她看到的夜莺并非园丁看到的那只,它们不过凑巧都出现在这里而已。
之后夜莺夜夜都来,与比阿特丽斯结成了知交。鸟是更苛刻的老师,声喉不知疲倦,一觉察她拉弓按弦的手有懈怠,立即拔高三个八度,夹之一连串小二度和增四度音程,表示它的不满(比阿特丽斯怀疑勋伯格作曲的灵感也是从它那里得来的)。它的声带构造必然是非人的,人眼无法逼视,人脑无法理解,甚至深刻地影响了她梦境的结构。凌晨四五点,她躺在那张螺旋弹簧承托型床垫上,感到自身陷入夜莺的鸣管之中,一条黑漆漆的管道,她不断旋转、滑落,最终落在一张粉色的膜上。膜每隔几秒就剧烈颤动,她被抛向半空,被四面八方而来的气流穿透,意识随之如烛火,一时明,一时暗:她想起在母亲子宫里的日子,想起母亲总会弹起那台三角钢琴,想起母亲在印度喜马拉雅山的阴影下慢慢枯萎。是她,怀中的生命,使得母亲抱着信念回到了英国。她那时候也是夜莺啊。比阿特丽斯沿着梦的甬道,破入梦的血肉,捉住了那块方形的核,是三十二年前的自己。她的负六个月二十一天。她知道自己长什么样,现今的她能透过夜色偷窥过夜莺。这种机会并不多,她常常只是由声音想象它的样子。它不过一枚网球大小,棕色尾羽细心地藏起来,圆凸凸的脑袋机灵地转动,跟她未出生时一模一样。当它胸前绒毛鼓起,肌肉驱动气压,强音涌出管道,它的尖喙就得张开一个直角,使音符个个蹦哒出来。音符划破夜空,跑在弓弦前面。音符生在音乐之前。这特殊的二重奏还有那么多听众:野兔跟着打滚,鼩鼱忘记了挖洞,连搬家的蚂蚁也迷醉,成群结队倒在半路上。
转眼到第二年,比阿特丽斯忽然有了个新想法,这妙处只得她一人独享,未免太遗憾了,要是全英国、全世界的人都听到这音乐,该有多好。她去联系了英国广播公司,双方一拍即合。那时候,完备的录音技术还没被发明出来,户外现场直播更属罕见,但公司负责人认为,这是值得的豪赌。很快,当时最先进的麦克风、马可尼-赛克斯磁力电话、十几公斤的大块头,开进了比阿特丽斯家的花园,伴随着几十条海蛇般的电缆,它们在灌木丛中缠绕出一个复杂的图案,延伸到放大器和远端的耳机上。直播那晚,比阿特丽斯拎着大提琴,像往常那样,坐在橡树下。技术人员无处不在,有的趴在草丛中,有的蹲在沟里,有的在树上,全神贯注不敢动,屏住呼吸。比阿特丽斯正前方的远处站着一位信号员史蒂芬,他点燃香烟,光芒在夜幕里一闪一闪,比阿特丽斯便驱动手里弓弦,演奏起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G大调弦乐四重奏》,乐符先感染琴身,渐向四周暗暗弥散开来。
但,夜莺失踪了。
这场事先张扬的召唤未起效。那只敏锐的鸟,或许早已察觉,它不愿飞过来,卡在了晨昏交替的夹缝里。比阿特丽斯演奏了半小时后,大家都感到了事情不对劲——苍蝇钻进麦克风,野兔咬断了电线,她家里的毛驴因见了生人,四蹄不安地踢踏,大声嘟囔,就连演奏者本人,也开始手心出汗,手臂虚浮,一颗心更沉不到底,她的确已感知到了鸟用缺席传达的怨恨,想必它觉得她出卖了它,她把它架在火上烤。如果她知道今夜之后鸟永不再来,她绝不会做这件蠢事,她会先用白马尾毛做成的弓弦勒死自己。但比阿特丽斯还是以极高的职业素养拉了下去。拉到一小时零十分钟时,守在收音机前未睡的最后一批听众突然听到了一声鸟鸣,那声音倚在琴声拉长的尾部,活泼地跳进来,跟着琴声上行,又顺着滑落。鸟声善变,就是在极高的音区,听众一时间也听出了六种交叠的声音,像是六只鸟齐鸣,实际上只是同一种声音急速变化的幻影;而鸟声凝成一股,唱出拉长音时,音符便如雨点拍打湖岸泛起的水泡,连缀不绝。这不像是世间的音乐,简直是神赐。兴奋的听众们忍不住打电话给亲朋好友,怂恿他们打开收音机,或者把话筒按在收音机喇叭上,逼迫他们一起聆听。嘘。安静。梦来了,一同坠入夜莺的鸣管之中吧。
这场神奇的夜间活动也是英国广播公司最成功的户外直播之一,在英国乃至欧洲引起了骚动,到一九二七年,大提琴与夜莺二重奏转录成唱片后,每年都会反复广播几次,直至一九四二年止。听众来信何止千万。一九四一年正月,一位住在伦敦城的听众一把鼻涕一把泪给广播公司写信,说多亏了夜莺之声,重振她的心灵,才令她挺过了去年泰晤士河退潮时德国人的空袭以及引发的大火。她亲眼见到二十九枚燃烧弹在空中闪过,那时家里的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白磷燃烧的光芒竟也被她视作悬着的圣光,其中一枚炮弹正中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结果并未引燃,拐个弯,顺势滑落下去。还有一位军队医院的护士来信说,伤员最多的那天,她就像漂浮在断肢残臂的海洋里,嚎叫和呻吟一浪接一浪,她是睡不着的,她不在乎,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伤员安眠呢?答案就在广播里,夜莺的鸣唱从圆盆电磁式喇叭流淌出来时,所有人都安静了。那一晚战士们都进入了梦乡,带着呓语,也带着完整的躯体。夜莺之声传播得越广,各种传言越离奇,到头来,它已经远远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演变为福音,是弥赛亚,是心理声学(psychoacoustics)的完美事例。可真相有谁知道?那一晚夜莺确实没有来。听众在广播或唱片里听到的,其实是一个女歌剧演员的声音,她以表演鸟叫而闻名。为避免直播事故,当时英国广播公司启动了应急预案。那个女演员悄悄走到比阿特丽斯身边,模仿夜莺的声音,一起完成了那个虚伪的二重奏。
那个女人叫克洛伊•塞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