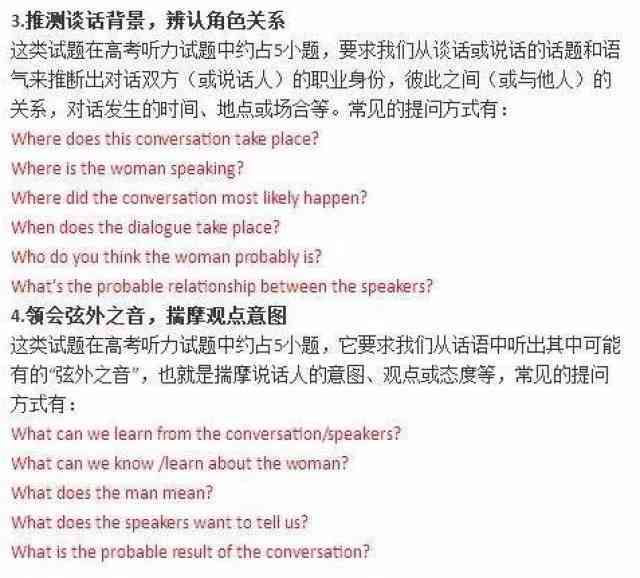塔市驿,是华容境内长江南岸一处古渡古驿,与湖北监利隔江相望。塔市驿始名塔子矶,因古代有一座江畔白塔而声名远播。白塔始建于北宋,初建三层,后加高到七层。当年白塔既为航标,又镇风水,以白塔为中心,华容、监利、石首长江两岸三县的商贾聚集于此,热闹非凡,被誉为“小汉口”,民间甚至有“华容弯塔市驿”之说。
历史的记载中,有塔市驿的众多身影。
绍兴人陆游《入蜀记》卷五,曾记其停泊于此:“挂帆抛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矶,江滨大山也。自离鄂州,至是始见山。买羊置酒。”那天是公元1170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四十六岁的陆游还向江边人家讨了几枝菊花,觉得“芳馥可爱,为之颓然径醉”。赏花饮酒之夜,江上落雨,“夜雨极寒,始覆絮衾”,陆游那晚是盖着被子睡觉的。
陆游在塔子矶停泊过夜,除日记外,还专门写有诗歌《塔子矶》:
“塔子矶前艇子横,一窗秋月为谁明?青山不减年年恨,白发无端日日生。七泽苍茫非故国,九歌哀怨有遗声。古来拨乱非无策,夜半潮平意未平。”(《剑南诗稿》卷二)
除陆游外,史载毛泽东也曾于1927年在塔市驿渡过长江,北去武汉。
后来白塔圮毁,加上陆路交通的发达,塔市驿趋于冷落。现在隶属于华容县东山镇的这个古老的江岸集镇,已经空旷少人。正对街心的一个很大的个体超市,将花花绿绿的各色商品摆放在门口,寂寞地等待买主。但从集镇留存的大小街巷,从街心旁那座已经翻修保护的高大礼堂,仍然可见塔市驿昔时的格局。
好在塔市驿重新振兴在望。为什么?因为华容人念念不忘祖宗的白塔,他们在白塔旧址又发愿重新建造了新塔。
重建之白塔被命名为云梦塔,重聚气场,更显气势,未到塔市驿,先见云梦塔。此塔既非宗教部门承建,也非政府投资,完全是由当地群众、寓外乡友捐资建成。在捐资功德碑上,一位据说是渔民家庭出身的华容企业家,个人就捐资100万元。
云梦塔2019年8月6日动工,2020年8月23日封顶。
我眼前的云梦新塔,高七层,八边形楼阁式,实木加砖混结构,塔四周围以大理石栏板。
以敬慎之心进塔,底层玻璃柜内珍藏陈列有白塔石顶遗物;塔的顶层则安放有毛泽东的纯紫铜像,高度与伟人生前身高相仿。
全塔气冲楚天霄汉,登塔顶而眺,蜿蜒长江,华容风物,皆历历在目。
在介绍云梦塔的资料上,我读到倡议捐资发起人、华容前辈赵焱森撰写的新塔联语:
高塔轩昂,梦泽新观,功德万方扬正义;
长河涤荡,周郎何处,浪花一卷笑虚名。
在塔市驿的中饭,我吃到了独特的籼米团子。据说这是江对岸湖北监利人喜欢的吃食。团子结实,个头很大,外表比糯米团子粗糙,其馅是将腊肉、豆腐干、酱萝卜等剁成丁块,再拌上多种佐料制成。蒸熟后,既可充饥,又可下酒。这是江上重体力劳动者的耐饥食物。一地食物,可见一地内在的生活与文化。
由塔市驿前往华容禹山途中,偶尔有野鸽子扑来车窗。一个又一个的村落、乡镇,散落在广阔楚地。起伏的田土上,桃花盛开,麦苗油绿,金黄的油菜花一派耀眼。华容是糯米团子之乡(地属江南证明之一种),沿途广告牌上别地难见的团子广告,不时掠过视野。
禹山,传说因大禹治水时登此山而得名。山上有古刹禹山寺。穿过重修的禹山寺,登小路上到山顶,还有古旧的禹王殿,传说此处的禹王菩萨十分灵验。在寺中,遇到僧人耀觉法师和尼师博缘,均为周边人氏,为“菩萨接引而来”。博缘师将禹王殿前的山顶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场边上,有一块已被风雨侵蚀模糊的水泥碑,上刻杜甫诗:“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
查阅后知,此《禹庙》诗系公元765年秋,杜甫出蜀东下,途经忠州(今重庆忠县)参谒忠州大禹庙后所作,非在华容禹山寺作。不过“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句,若在秋季,倒也和华容禹山寺之景象高度吻合。
晚上住华容县城,一夜安睡,晨间即起。烧水喝茶后出房间,找空僻处活动身体后,即在华容的晨街漫步。住地距县城汽车站很近,站前空地边上就停有一辆“华容—石首”的中巴车,有女人和站在车旁的司机问答后便上了车。进售票处看了一下,华容每天有开往张家界、常德、益阳、沙市等地的车,但班次最多的目的地,是石首、长沙和岳阳高铁站,基本是半小时或一小时一趟。
湖南的华容和长江对岸的湖北监利一样,有独特的早酒文化。当地男子习惯早晨“先晕个二两再说”。果然,在汽车站附近的范蠡路上,一家叫“混日子酒店”的店门前,就有两个男人坐在露天的矮桌上,已经喝开了酒。而北支路上,早餐早酒的店铺更多更丰盛。一家店堂宽大干净的早酒店门口,贴有这家店的菜品介绍,分“特色卤菜”和“小火锅”两大类。另外还特别注明:经营早中晚,经营各种小炒。真是非常诱人。除早酒店外,华容街头还有很多团子店,一家名叫“湘糯情”的团子坊生意兴隆。华容人对团子,确是真爱。
从“混日子酒店”到北支路,我是顺着范蠡路走的。华容这条路以越国名臣“范蠡”命名,引起了我的好奇。经查,古代文献上竟然有范蠡墓在华容的记载,明代《华容县志》提到:“城西田家湖上,有范蠡墓”;《晋书·地道记》说:“陶朱冢在华容县”。而我所知道的,是山东有范蠡定居终老菏泽定陶的遗迹与传说;我的老家江苏宜兴,也有蠡墅、蠡河(我从小就是喝蠡河水长大的)、施荡等和范蠡密切相关的遗迹。看来,范蠡是大智慧人,他辞别勾践后,摆下迷魂阵,真真假假,保证了他隐于江湖,安全终老。
离开华容,辗转向东南方,前往湘、鄂、赣三省交界区域,隶属于湖南的平江县。
平江首先让我震撼的,是天岳幕阜山。
天岳,天之岳,山名何其气派!海拔1596米的天岳幕阜山,是湘鄂赣三省边界第一高峰(主峰在湖南平江境内),它被道家尊为第25洞天,传说还是造人的伏羲女娲的婚居地,他们婚后选择了天岳作为生活的家,所以,我们是否能够说:湖南天岳,是传说中人类的起源地?
五岳之外有天岳。但天岳谦逊,其高度与五岳相较,东岳泰山(1532米)、西岳华山(2155米)、南岳衡山(1300米)、北岳恒山(2016米)、中岳嵩山(1512米),是携手共进的亲密关系。
在天岳幕阜山,我还获知了“岳阳”之名的由来。水之南曰阴,山之南曰阳,因为岳阳古郡治在天岳之南,所以得名岳阳。
坐缆车上山,感觉山极高峻,坐缆车的时间似乎远超庐山、黄山。山脚下还是好天气,缆车升到半山腰,始有雨雾。俯视身下山谷间,有一棵开得自在的野山樱,很美。等到了山上,四周完全是雾雨白茫,于是穿起雨衣。
天岳山上有神奇的“白龟沸沙池”,是石块垒成的大池,有台阶可以近水。泉眼喷涌,细沙如沸。伏羲于天岳无处不在,传说他在池中曾养有白龟,受白龟背上纹路启迪,画出了八卦。当地民众敬重此池,称男人喝了身体健康,女性喝了求子得子。从湿滑台阶走下去,捧喝沸沙池泉两口。身旁的山中松树皆在雨雾中,宛若白汽轻拂间偶显其身的一众仙人。
继续上行,天岳之巅有人造的“观天台”。沿旋转楼梯登到台顶,带有水雾的大风猎猎,吹人欲倒。这里是天岳幕阜山的最高处,晴天时可眺三省,然而此刻一派白茫,什么也不见。雨雾浩茫连广宇,转念间我想,这种什么也不见的一派白茫,恰恰应了神秘的“天岳”之名:立于观天台顶,什么也不见,但也完全可以说是一切尽见。
平江带给我的另一个震撼,是在平江的汨罗江畔,我瞻仰到了伟大的唐代诗人、诗圣杜甫的初葬之墓。
坊间多称杜甫是死于湘江舟中,而到了平江,我才知道,事实是:杜甫和他的前辈屈原一样,肉体的生命终结于汨罗江上。
我们可以简略梳理一下杜甫生命最后一年的大致轨迹。
公元770年四月八日,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潭州(长沙)刺史兼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崔瓘,发生兵乱。杜甫这时正在潭州,事变发生在夜里,所以他也不得不“中夜混黎氓,脱身亦奔窜”,混迹于百姓中,开始向衡阳逃难。
这时,杜甫的舅父崔伟在郴州做录事参军,写信让杜甫去郴州。由衡阳南赴郴州途中,杜甫阻水于耒阳方田驿,食物耗尽。耒阳聂姓县令馈杜甫以“牛肉白酒”。杜甫曾写诗记此,诗题如叙事:《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
六月,潭州兵乱被平定,杜甫北归心切,遂改变原来南下郴州投奔舅父的计划,又由耒阳向北折返长沙,准备“归秦”。回到长沙,杜甫写有《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这首诗。
公元770年冬,杜甫由长沙往岳阳,正式开始北归故里。杜甫的孤舟由湘江入洞庭湖,遇寒风恶浪,重疾复发,在船上写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其中的“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一句,已见生命的凛凛寒气。此时此景下,杜甫由洞庭溯汨罗江而上,往昌江(今平江县)投友求医。不幸的是,一代诗人竟病逝于平江汨罗江上,遂就近安葬于今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小田村。
比杜甫小六十七岁的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记载有:杜甫“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
杜甫落葬平江后,其子杜宗武、孙杜嗣业留下守墓,平江杜氏自此繁衍。《杜氏族谱》载:平江杜姓源于京兆郡,杜甫为开基始祖。至宋代,丁口鼎盛,人才辈出。自宗武一世至今已传六十余代,目前平江杜姓有两千余人。
我来到的平江小田村,不仅有杜甫墓,还有杜甫祠(杜文贞公祠),墓和祠均始建于唐。早在1984年,此杜甫墓就被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词典》认定为全国唯一的杜甫墓葬。
杜甫墓早期为花砖结顶,红石墓碑,唐墓形制。现在我眼前的简朴墓园已是清光绪年间重修,改用扇形麻石结顶,碑换青石,碑文为:“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之墓”。因北宋时杜甫被追谥为“文贞”,故后世也称他为“杜文贞公”。杜甫祠的门额上,有这样四个大字:“诗圣遗阡”。遗阡,即坟墓之意。
现在的墓祠内,仍保存有唐代红砂岩覆盆式莲花柱础(为保护,已用玻璃罩住)、唐代卷草纹墓砖等实物,历史文化信息真实丰富。
我置身的杜甫墓地,气息安详。杜墓周围有砖砌墓墙,墓墙后是栽种青柏的坡地。放轻脚步上去,我数了一下,一共生长有二十三棵高大的柏树。青郁的柏树在汨罗江畔相伴诗圣,象征着诗之生命的长青。
汨罗江,这条发源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龙山梨树埚(属江西修水县境)、最后在岳阳汇入洞庭湖的南方之江,是伤痛而伟大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二百五十三公里,但是它收藏了中国诗歌史上的诗祖屈原和诗圣杜甫,所以,我心中的汨罗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诗歌之江。
这次湘楚之行的辞别地,是长沙。三月,初春,长沙的雨晨如暗暮。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座诞生了贾谊、欧阳询、怀素、谭嗣同、田汉,发掘出马王堆老子帛书的华中古城,在我离开的早晨,正下着潇潇的暗色之雨。春雨中,汽车启动最高档的雨刮器稳稳行驶。身边的侧窗上,雨水持续滑落,如一条条微型的长江和汨罗江。前方,那个明亮干燥、超大型的现代交通公共空间内,有我暂且不知的、凝定的电子汉字标语默默等待着我,它们是:“知足长沙乐”“湘见恨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