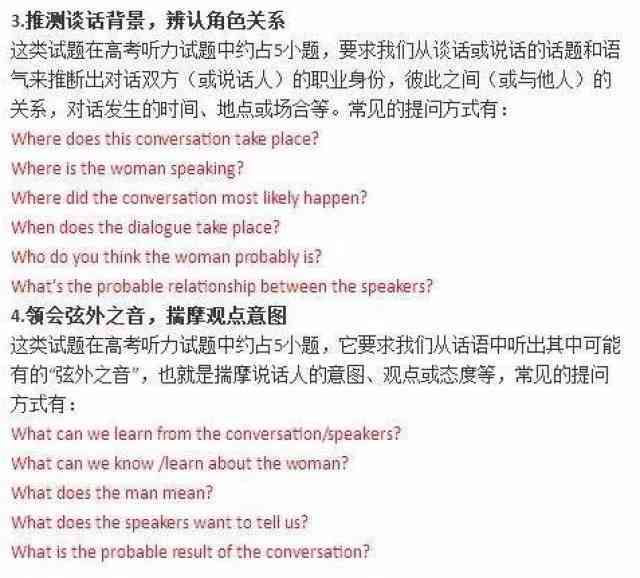潮新闻客户端 周国良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星空中,有多少璀璨的星辰因时光的尘埃而黯淡?有多少值得铭记的生命因缺乏记录而消散于虚无?徐安贞——这位唐代“德行宗师”“文辞雄伯”,在正史中仅留下模糊身影的贤臣文人,经由陈建群先生历时多年的文学考古与艺术重构,终于在他的新书《大唐传奇徐安贞》(2025年6月,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小说中,获得了丰满的血肉与生动的灵魂。
这部作品不仅填补了金华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空白,更开创了一种将严谨史学考证与文学想象、美学重构完美结合的传记写作范式。当读者跟随作者的笔触穿越回那个辉煌与危机并存的开元、天宝年间,所遇见的不仅是一位古代士大夫的宦海沉浮,更是一幅金华地域文化在唐代的精神地图;一种超越时空的文人风骨与乡土情怀的深刻对话;一场文明与野蛮的直接碰撞、正义与邪恶的正面交锋。
被历史遮蔽的先贤,徐安贞其人其事的重新发现
徐安贞是谁?对于大多数现代读者而言,这个名字恐怕极为陌生。即便在专业史学界,关于这位唐代官员和文人的研究也相对匮乏。《全唐文》中仅存其拟就的几篇制文,《全唐诗》收录其诗作11篇,《旧唐书》《新唐书》记录也不多,明代童佩辑有《徐侍郎集》,除此之外,便是散见于地方志中的零星记载。正如陈建群在创作谈中所言,他最初接触徐安贞这一历史人物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心灵“震惊”——为何这样一位被唐玄宗誉为“德行宗师”“文辞雄伯”的重量级人物,会在历史长河中几近湮没?这种震惊转化为一种文学使命感,驱使他深入挖掘这位先贤被遮蔽的人生故事。
徐安贞(671-743)的一生,恰逢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初名楚璧,字子珍,信安龙丘人,因行政区划调整,其故宅位于后来的汤溪县(今浙江金华婺城区东祝、黄堂一带)。这位金华子弟少时就读于九峰山,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中进士,开启了仕宦生涯。从武陟县尉起步,在县尉任上铲除村霸、发展农业,受到朝廷及乡民的肯定。后来参加皇帝制考(由皇帝亲自出卷的考试),没想到三个科目(每次制考科目数不一样,大概在三至六个左右)他都考了第一名,于是徐安贞“一岁三甲”的事迹上了大唐热搜,成为当时读书人的楷模。制考时,任何一个科目能得第一就已非常难得,何况徐安贞是三个科目第一。由此受到年富力强的唐玄宗格外赏识。“选入殿判正,补丽正学士”,成为起草诏令的近臣,后赐今名“安贞”。历任起居舍人、检校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中书侍郎等要职,深得唐玄宗信任,每每委以重任,徐安贞从“不负圣望”,出色完成任务。
抱负远大的徐安贞在此期间与张说(宰相)、张九龄等人一起选拔、培养大量能臣与吏才,使得国家日益强大,百姓生活有了转机。徐安贞既是开元盛世的见证者,也是开拓者。然而,唐玄宗年老后宠信奸臣李林甫,在李专权时期,徐安贞不愿同流合污。宰相张九龄罢相后客死他乡,徐安贞在为昔日好友、政治同盟写完墓志铭后,毅然选择回到故乡九峰山隐居。70多岁高龄时,于九峰山创办“安正书院”,教育后人勤奋读书,有所作为。据学者考证,“安正书院”是当时南方一带最早书院之一,从某种意义而言,“安正书院”就是浙学之本、婺学之根。
这样一位集政治才干、文学造诣、实干能力与高尚品德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理应在唐代文化史上占有更显著的位置,却因种种原因被主流历史叙事边缘化,这实在是一桩憾事。
陈建群生于斯,长于斯,他以一名记者、文学创作者、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多重身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不公,并以文学的方式予以纠正。在《大唐传奇徐安贞》中,他不仅依据《全唐文》《全唐诗》等传世文献,更深入挖掘万历《汤溪县志》《徐氏族谱》等地方史料,并踏访金华、兰溪、龙游一带与徐安贞相关的古迹遗址,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素材。这种跨学科的准备工作,使得小说在史实基础上展开的文学想象具有令人信服的厚重感。尤为珍贵的是,作者将徐安贞置于金华地域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审视,揭示出这位唐代文人官员与故乡之间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九峰山的求学经历塑造了他的学识根基,金衢地区的民风民俗滋养了他的道德情操,即便在朝廷位居高位时,这种乡土纽带也从未断裂。当政治理想受挫时,他最终选择的归隐地不是别处,正是少年时代求学的九峰山,完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归根。
通过重新发现徐安贞这一被历史遮蔽的先贤,陈建群的传记小说实际上在进行一项文化记忆的抢救工程。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曾提出“记忆之场”的概念,指出某些人物、地点或事件如何成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徐安贞对于金华地区而言,正是这样一个被遗忘的“记忆之场”,通过文学再现,他不再只是古籍中的冰冷名字,而成为连接当代读者与唐代金华的文化桥梁。陈建群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八世纪金华士人精神世界的窗口,这种地方文化史的挖掘与重构,对于增强地域文化认同、丰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史实与虚构的辩证,传记小说的叙事艺术探索
传记文学自古以来就面临着“实录”与“艺术”的两难选择。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史传传统,同时也运用丰富的文学手法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而现代传记小说则更加自觉地探索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辩证关系。陈建群既不拘泥于史料的字面真实而牺牲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不为追求戏剧效果而随意扭曲已知历史事实,而是在充分尊重历史框架的前提下,以合理的想象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使千年之前的人物重新获得呼吸与温度。
细读作品,我们可以清晰辨识作者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匠心。对于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重要历史事件,如徐安贞中进士、任职丽正学士、起草重要制文、升任中书侍郎以及最终归隐等人生节点,小说严格遵循历史记载;而对于史书中语焉不详的细节——如徐安贞少年时代在九峰山求学的具体情景、他与同僚友人的日常交往、面对李林甫专权时内心的矛盾挣扎、隐居期间的精神状态等——作者则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行合乎历史情境的艺术重构。这种创作方法恰如钱钟书所言“史家追叙真人实事,必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既保证了作品的历史可信度,又不失其文学感染力。
在叙事结构上,陈建群采用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与西方现代传记技巧相融合的方式。全书以徐安贞的人生历程为主线,大体遵循时间顺序,但又不时穿插倒叙、预叙等手法,在保持故事流畅性的同时增加叙事的层次感。每一章节既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单元,又是整体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结构既照顾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又避免了传统线性叙事的单调性。作者还巧妙地将金华地区的民间传说、风物掌故融入主体叙事,如九峰山的来历传说、当地农耕习俗等,这些“婺文化元素”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地方色彩,也为历史人物提供了鲜活的文化背景。
陈建群对传记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索,最根本的特点在于他始终将徐安贞视为一个复杂立体的“人”而非简单的历史符号。在史料记载的公共形象背后,小说深入挖掘其作为学子、官员、文人、隐士、先贤的多重身份,展现他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希望与恐惧、坚持与妥协、得意与失落。这种“同情之理解”的写作姿态,使得笔下的徐安贞既有历史人物的厚重感,又有文学形象的生动性,为当代传记文学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婺文化的文学再现,地域特色作为叙事资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文学历来重视地域文化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塑造作用。从《诗经》的十五国风到现代文学中的京派、海派、山药蛋派,地域特色始终是作家们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陈建群深谙此道,在《大唐传奇徐安贞》中,他不仅讲述一位唐代官员的故事,更通过这一人物全面展现金华(古称婺州)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使作品成为婺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一次精彩亮相。
小说中婺文化元素的运用首先体现在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描写上。金华地处金衢盆地,素有“浙江之心”之称,境内有婺江流淌,九峰山耸峙,山水形胜独具特色。陈建群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徐安贞少年时代生活的自然环境:“春日的九峰山,杜鹃花开得正艳,像一团团火焰燃烧在翠绿的山腰间;婺江的水清澈见底,鱼儿在鹅卵石间穿梭,岸边有农人在耕作,在说笑……”这些饱含地域特征的景物不是简单的背景板,而是与人物成长密不可分的精神摇篮。九峰山既是徐安贞求学的实际场所,也是他日后遭遇政治挫折时回归的精神家园;婺江之水则成为连接游子与故乡的情感纽带,即便在长安为官时,梦中的江水仍会流淌进他的诗行。这种将人物与乡土紧密联系的写法,超越了简单的地域色彩呈现,达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文人”的深刻表达。
其次,小说生动再现了唐代金华地区的民俗风情与社会生活。通过徐安贞这一视角人物,读者得以窥见八世纪婺州地区的农耕方式、饮食习俗、节庆活动、民间信仰等文化细节。例如,书中描写徐家参与当地“开秧门”仪式的场景:“安贞父亲领头,面向东方三鞠躬,然后下田插下第一把秧苗,口中念念有词,祈求风调雨顺。随后,帮工们纷纷下田,田埂上摆放着自家酿的米酒和刚出锅的清明馃。”这类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基于作者对金华传统民俗的深入研究,虽描写唐代生活,却能与今天金华地区保留的某些古老习俗相互印证,形成一种古今对话的奇妙效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未将古代民俗浪漫化或奇观化,而是将其作为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环境因素——正是这种浸润着农耕文明务实精神与自然崇拜的乡土文化,塑造了徐安贞为官时重视农桑、体恤民生的施政风格。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陈建群在小说叙述语言上的探索尤其值得称道。他创造性地将现代白话文与金华方言特色词汇、句式相结合,形成一种既通俗易懂又别具地方韵味的叙事语言。在人物对话中,他适当融入一些至今仍在金衢地区使用的方言词汇(如“侬”表示你、“嬉”表示玩),既增强了历史真实感,又避免了过度使用方言造成的阅读障碍。更为精妙的是,他将金华地区口语中特有的委婉表达方式和修辞习惯转化到叙事语言中,使整个作品的叙述节奏和语气都带有淡淡的“汤溪味”“婺味”“浙味”。这种语言上的地域特色不是浮于表面的装饰,而是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它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文化气场。
婺文化作为浙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其核心是务实求真、经世致用的精神传统。徐安贞身上体现的“清才特达”与“雅量深沉”的结合,正是这一精神传统的具体表现。小说通过大量细节展现他如何将金华士人的务实作风带入朝廷政务:在“司水土”时注重实地考察,了解农民实际需求;在“典图书”时不仅完成官方交办的编纂任务,还主动整理《文府》二十卷,为文化传承尽心尽力。即便在隐居期间,他也没有完全脱离社会,而是通过教授生徒、编修地方文献等方式继续服务乡梓。陈建群通过徐安贞这一形象,实际上勾勒出了婺文化在唐代的精神图谱,为当今金华地区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历史纵深。
唐代士大夫精神的当代观照
通过《大唐传奇徐安贞》这部作品,作者不仅再现了一位唐代官员的仕宦历程,更深入探讨了传统士大夫在“道”与“势”之间的艰难抉择,这一主题对于思考当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徐安贞的为官之道体现了典型的儒家士大夫理想。从孙逖(696年~761年,字子成,山东聊城人。唐朝大臣,学穷百家,善于属文。天宝年间,权判刑部侍郎,累迁太子詹事)所撰《授徐安贞中书侍郎制》中“清才特达,雅量深沉,为德行之宗师,是文词之雄伯”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受到玄宗器重,正是因为兼具文学才华与政治能力。小说通过多个情节展现他如何将文学修养转化为施政智慧:起草诏令时,他注重文辞的准确与庄严,体现朝廷威仪的同时不失对臣下的体恤;审理案件时,他善于引经据典,以文化力量化解民间纠纷;选拔人才时,他既看重应试者的文采,也考察其实际办事能力。这种“文心”与“吏才”的结合,正是盛唐时期精英政治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为理想化的官僚形象。
唐朝开元盛世转向天宝衰落的转折点上,李林甫专权,朝堂噤若寒蝉。品读《大唐传奇徐安贞》你会发现,作者用了几个章回的篇幅来写徐安贞与张九龄及李林甫之间的故事,这也是这部传记小说的重点。张九龄作为一代贤相,以刚直敢谏而著称,也因此早就成了李林甫的眼中钉,在李林甫的陷害下最终罢相,郁郁而终。彼时,满朝文武慑于李林甫之威,无人敢为张九龄发声,唯有时任中书侍郎的徐安贞挺身而出,为其撰写墓志铭。此举不仅是对挚友的深情悼念,更是在政治高压下对正义的坚守,展现了古代士人的铮铮风骨。
墓志铭原文如下:
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志铭并序
太中大夫、守中书侍郎、集贤院学士、东海县开国男徐安贞撰。
公姓张氏,讳九龄。其先范阳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公诞受正性,体於自然,五行之气均,九德之美具,才位所底,不亦宜欤。盖所阙者降年之数不延,苍生之望未足耳。源以秀才。没赠都督,历任典诏翰,居连率,自中书令而迁端右,凡十八徒焉。序乎官次,存乎事迹,列於中原之碑,备诸良史之笔矣。公之生岁六十有三,以开元廿八年五月薨,廿九年三月三日迁窆於此。韶江环浸,浈山隐起,形胜之地,灵域在焉,神其安之,用永终古。呜呼!嗣子拯号诉罔逮,而谋远图,刻他山之石,志於玄室,人非谷变,知我公之墓於斯。铭曰:龟筮从兮宅其吉,山盘踞兮土坚实。呜呼相国君之墓,与气运而齐毕。
李林甫执政时期,“口蜜腹剑”的权术使朝臣人人自危。《资治通鉴》载:“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他排斥异己,大兴冤狱。张九龄因反对重用蕃将、抵制废太子之议,最终被贬荆州,客死他乡。其死后,李林甫更严禁朝臣悼念,以免动摇自己的权威。在此背景下,徐安贞的选择极具风险。墓志铭虽为私人悼文,但在政治高压下,任何对张九龄的褒扬都可能被视为对李林甫的挑战。徐安贞身为中书侍郎,深知其中利害,却仍执笔为故友正名,其勇气堪比东汉时期不畏董卓之威、为友人收尸的蔡邕。
徐安贞所撰墓志铭虽未直接指斥李林甫,但字里行间暗含深意。他称张九龄“九德之美具,才位所底,不亦宜欤”,此处是作者对张九龄的气质、品德、才华、地位极尽溢美之词。大赞其人品,暗指其遭贬的真相。更意味深长的是,他强调张九龄“存乎事迹,列於中原之碑,备诸良史之笔矣”,既是对张九龄政治操守的肯定,亦是对李林甫“以术驭下”的无声批判。这种隐晦的抗争,恰是古代士人在强权下的智慧。司马迁曾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徐安贞选择以文字为武器,既保全自身,又为历史留下真相。其墓志铭不仅是对逝者的纪念,更成为后世评判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徐安贞之举体现了儒家“杀身成仁”的精神内核。历史终将证明,真正的权威不源于强权,而源于人心。李林甫虽能一时钳制言论,但其恶行终被《旧唐书》评为“妒贤嫉能,蔽塞言路”。而徐安贞为张九龄题铭的壮举,则与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宣言一样,成为士人风骨的永恒象征。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一个人的正直或许微弱如萤火,但正是这微光,照亮了后世对公理与良知的信仰。千年之下,徐安贞的笔墨丹心仍提醒我们:面对不义,沉默即是屈服;唯有坚守道义,方能无愧于历史与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将徐安贞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道德符号。在表现他坚守原则的同时,也揭示了他作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面对朝廷的腐败,他最终选择的是个人化的隐退而非公开的抗争;归隐后虽保持清高,但对国家政治的直接影响已大为减弱。这种复杂化处理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也引发读者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边界的思考——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士人应当如何平衡个人操守与社会影响?保全清白与积极抗争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徐安贞的故事对于当代知识阶层仍具有重要的观照意义。在一个价值多元、利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独立人格与社会参与的平衡?专业能力与道德担当如何相得益彰?面对不完善的政治生态,是选择“独善其身”还是努力“兼济天下”?作者虽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对徐安贞生平的艺术再现,为读者提供了思考这些永恒命题的丰富素材。通过历史人物这面镜子,我们得以更清晰地审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与道德选择。
传记文学的创新与地方记忆的重构
《大唐传奇徐安贞》作为一部当代传记文学作品,其意义不仅在于复活了一位唐代文人的形象,更在于它探索了一种融合地方性知识与主流历史叙事的写作路径。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地方志、家谱、碑传等文本形式一直承担着记录乡土历史的功能,但这类写作往往受制于固定格式而缺乏文学感染力;而主流历史叙事则容易忽视地方性人物与事件的价值。陈建群的创作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将金华地方文化记忆以文学形式融入国家历史的大图景中,为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这部作品对地方记忆的重构具有多层次的意义。首先,它填补了金华地区唐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空白。作为“九峰三贤”之一,徐安贞在地方文化谱系中理应占有重要位置,但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深入的介绍。作者通过多年的史料梳理和文学创作,使这位被遗忘的先贤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丰富了金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层内涵。其次,小说将官方正史与地方民间记忆有机结合,构建了一种立体化的历史认知方式。书中既有基于《全唐文》《旧唐书》等官方文献的严谨史实,又吸收了金华地区关于徐安贞的民间传说(如其少年聪慧的故事、归隐后的逸闻等),这种“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打破了单一历史视角的局限性。第三,作品通过文学想象激活了地方文化景观的历史记忆。九峰山、婺江、徐宅山背等实际地理空间因与徐安贞生平的联系而获得新的文化意义,成为连接古今的“记忆之场”,这对于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归属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传记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大唐传奇徐安贞》的探索性体现在几个方面:它突破了传统传记写作要么严格遵循史料、要么天马行空虚构的二元模式,创造了一种基于深入研究的有根据想象;它将个人生命史与地域文化史有机结合,展现了个体如何在特定地理文化环境中成长并反哺这一环境;它尝试在严肃历史主题与可读性强的文学表达之间寻找平衡点,使专业研究成果,能够以雅俗共赏的形式传播给大众读者。这些创新不仅对地方先贤传记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也为整个传记文学如何更好地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唐传奇徐安贞》的出版,还引发我们思考地方文化记忆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机制。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许多地区面临着文化同质化与历史记忆断裂的危机。通过文学形式挖掘、整理、传播地方历史名人的故事,是一种有效的文化记忆保存与传递方式。陈建群作为金华本土作家,对家乡历史文化有着深厚感情和独到理解,这使得他的创作既有学术研究的严谨,又有乡土情怀的温度。当读者、尤其是金华地区的年轻读者通过阅读这部作品,了解到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曾有过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先贤时,产生的不仅是对历史的兴趣,更是一种文化自信与传承责任。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地方文化建设的深层意义所在。
《大唐传奇徐安贞》的更大启示或许在于:中国文化是由无数地方文化脉络交织而成的宏大图景,只有充分重视各个区域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才能真实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作者通过一位金华先贤的传记小说,实际上参与了一项全国范围内的文化记忆重建工程,这项工程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复古怀旧,而是从地方历史资源中汲取智慧,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根基与精神资源。
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灵魂对话
合上《大唐传奇徐安贞》的最后一页,徐安贞这个原本陌生的历史人物已然在读者心中留下鲜活印象。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一个金华少年如何通过勤学成长为朝廷重臣,又如何在政治漩涡中坚守士人风骨,最终回归故乡创办“安正书院”福泽乡里的心路历程。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精湛的文学技巧,完成了一次跨越千年的灵魂对话,使这位被历史尘埃遮蔽的唐代先贤重新焕发光彩。
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塑造,更在于它探索了一种处理历史素材的文学方法论:在严格尊重已知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使冰冷的历史数据转化为有温度的生命叙事。这种创作方法对当下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和地方文化挖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小说将个人命运置于地域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的视角,也为文学如何参与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范例。
《大唐传奇徐安贞》最终实现的是一种双向的文化寻根,既是当代金华人对本土历史名人的重新发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语境下的再次确认。当读者跟随着徐安贞的人生轨迹,思考文人与官僚、理想与现实、中心与边缘这些永恒命题时,实际上也在反思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与选择。这种借古鉴今的阅读体验,正是优秀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
在快餐文化、碎片阅读盛行的今天,作者耗时多年潜心研究、精心创作这部传记小说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坚守:不急功近利,不哗众取宠,而是以匠人精神打磨每一处细节,以敬畏态度对待每一份史料。这种创作姿态恰与徐安贞“清才特达,雅量深沉”的精神气质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也正如陈建群所言“创作,就是学习的过程”。或许,这才是《大唐传奇徐安贞》留给我们的最珍贵遗产,在浮躁的时代里,如何保持文化的定力与深度;在变革的浪潮中,如何守护精神的家园与根脉。(作者系金华市文史馆馆员)
本文作者周国良在阅读《大唐传奇徐安贞》